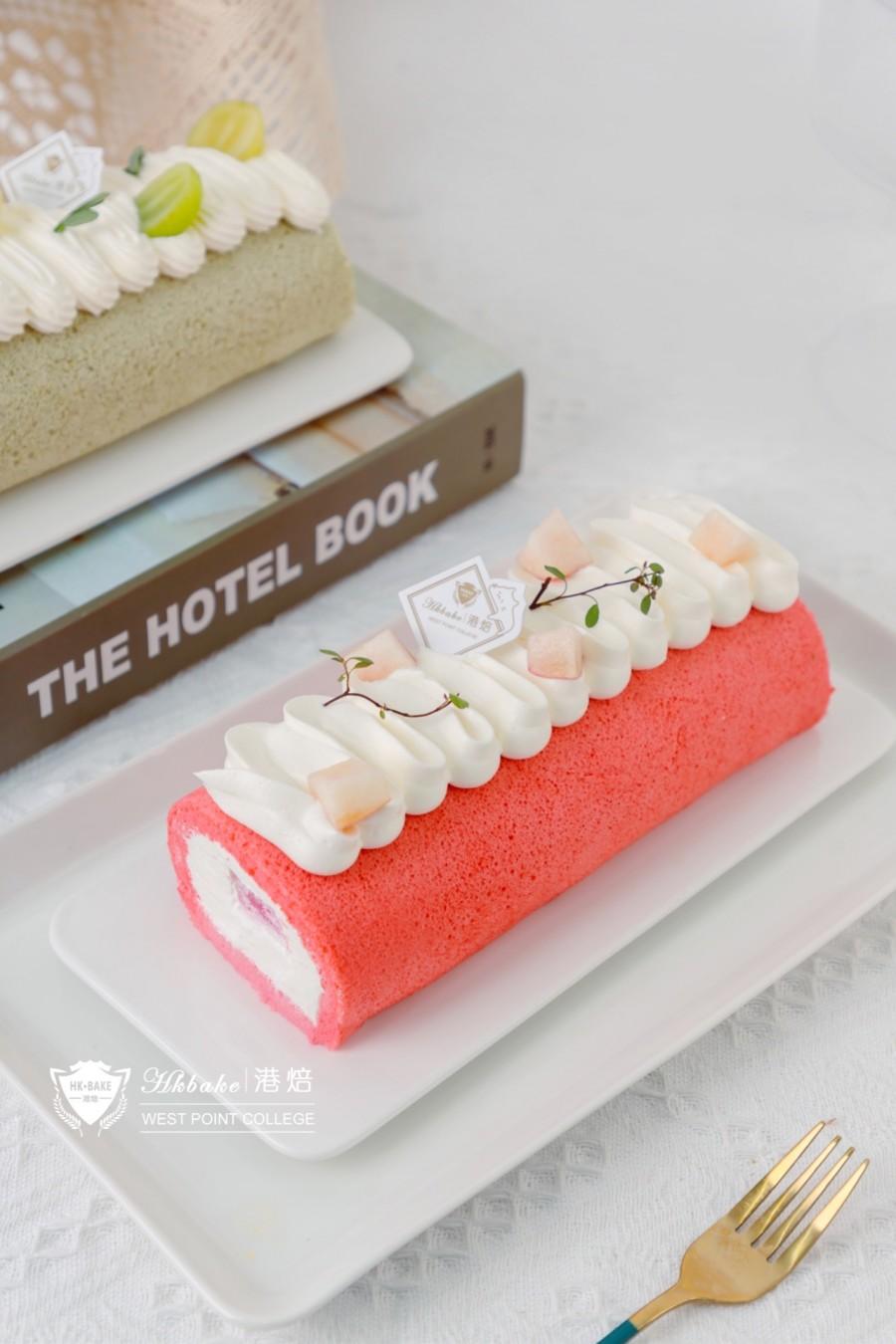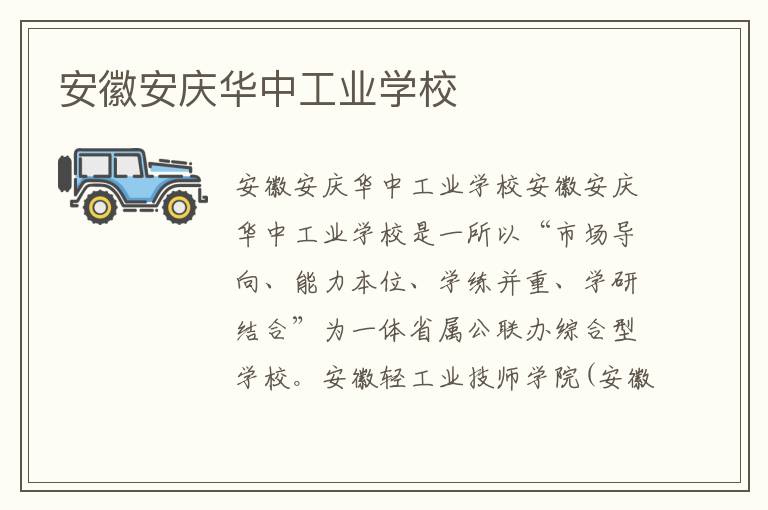送父親父親節禮物((20)父親之死)

父親節給父親的禮物(
20)父親的死亡(

1)父親節給父親的禮物xx年xx月xx日公元是我一生都不會忘記的一天我平凡、忠誠、善良、勤勞、樸實、默默無聞、毫無爭議的老父親在xx年的生命后去世了。
那是xx年夏至后的第八天,我們當地的夏麥收正在進行,那一天,我準備在一塊我們叫河東的土地上收割小麥,夏天的天空是晴朗的,我和妻子早早起床,簡單地洗了一下,我發動了我的嘉陵50摩托車,準備和妻子一起去地里收割小麥。
平常的日子里,老父親已經早早的起床打掃院子,喂雞喂羊,可是那天天已經亮了,院子里也沒有看到老父親的臉,我不禁懷疑老父親是不是睡過頭了,可是我卻沒有去想,因為我急著要下田。
正當我推著嘉陵妻子拿著鐮刀要出院門的時候,突然之間,我繼母從他們住的房間里慌慌張張地奔了出來,連連叫著我的小名;
“xx,xx你快看一下你大(當地土話指父親)呀!

那是怎么了!
”
“怎么了?
”我隨即問繼母,隨即將嘉陵支起,隨即奔到老父親住的房間,一看老父親躺在炕上,臉色紅潤,但眼不睜,口不言,摸摸頭,揣揣手,似有體溫,但不論怎么叫喚,就是一言不發,好像安詳的睡著了一樣。
見此情形,我不免也發慌了,急忙對繼母與妻子說道;

“不要慌!
你們先看一下,我去叫醫生!
”隨即,急匆匆地奔到了院子里,發動起嘉陵朝我們村里的醫生家馳去,好在醫生家也不遠,一時三刻,就將醫生請到了我們家。
但醫生進來看了看,摸了摸脈搏,試了試心臟,翻了翻眼睛,便說道;
“不用看了,準備后事吧!

”
見此情景,我看醫生也是回天乏術沒有辦法了,不由得悲從心來,一輩子忠厚老實,辛辛苦苦,剛剛過上了不多幾天不愁吃,不愁穿的舒心日子,況且上年才過了八十大壽,我們還沒有好好的孝順,侍奉您老人家,怎么說走就走了呢!
這可真是老話說得“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呀”!
而且,一生默默無聞,走時竟然也是默默無聞,沒有給我們留下只言片語。父親走得安詳,但也是我始料不及的,父親平時也沒有什么大病,只是有些哮喘病,早一天還在院子里幫助我們晾曬收割回來的小麥。
不過父親雖然沒有文化,但是一個忍辱負重不事張揚的一個人,有什么病痛從來不會在我們面前流露聲張,只是自己一個人默默地承受。

或許是父親真正的累了,想休息了!
再多的牽掛也挽留不住了!
父親走得很倉促,令我非常遺憾,但也算是無疾而終,在上世紀xx年代的時候也算是高壽而終,而也有的鄉親們說這是老漢家平時行善習好了,沒有受罪,無疾而終,這也給我的悲傷中平添了些許慰藉。
盡管父親是一個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老百姓,一生也沒有什么大作為,但在我心里,父親是一個正直大寫的人,一個寬厚善良的人,一個誠實守信從來也不為自己只想的一個人,是我心中的慈父,回想起父親的點點滴滴,無數的場景,都使我永生難忘!
父親走得很平靜,很安詳,如同夏日午后的一段小憩,隨夢而逝,擺脫了世事的纏繞,駕鶴西去,只留給我留下無盡的思念,也讓我們明白,人的生命,脆弱的如同風中的燭火,轉瞬即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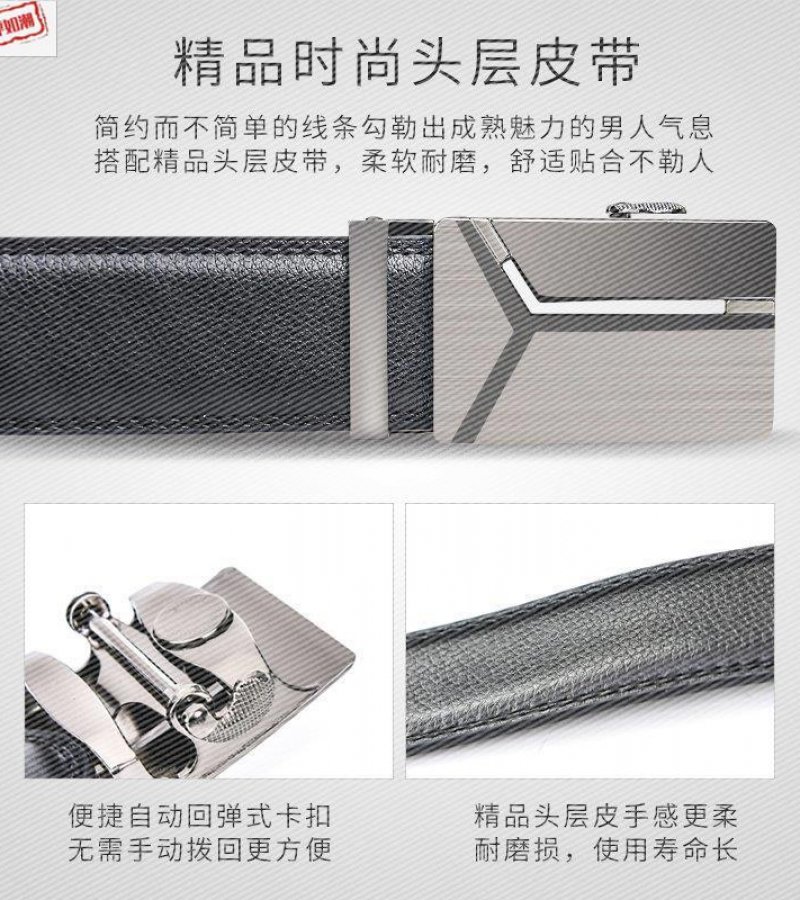
父親就這么突然走了,卻依然讓我悲痛不已,著父親漸涼的面頰,將再也見不到父親不管在那里見到我及孩子們那默默微笑的場景,而父親也聽不到我的孩子們扯著嗓子叫給他說話的情景了。
從此以后,陰陽相隔,永無相見之日,那真是子欲養而親不在,那種無盡的思念和痛楚,撕心裂肺。但不知為什么我竟然一聲沒哭。
或許是像哲人說的那樣,大愛無言,大悲無聲;
也或許是我不相信父親這一走就永遠不會再回來了。
以前參加別人的葬禮,看到挽聯上寫著音容宛在,意思明白,卻沒有什么稀豪感覺,但現在,我才領略到這四個字在我的心中,沉甸甸的,重如泰山!

我看醫生回天乏術,況且我平常也是經常在鄉親們紅白喜事上幫忙,也經歷過了不少事情,對于人的生死也看得開。
于是,我謝過了醫生,轉而通知了我的一些要好朋友,又將我岳母請了過來,岳母也是本村的,因為我岳母也是經常在左鄰右舍,親戚朋友們的紅白喜事上幫忙,她也懂我們當地紅白喜事上的一些風俗習慣,而且會經由(經由土話指招呼)。
而此刻,一些左鄰右舍,街坊鄰居得到消息,也不約而同地過來幫忙了。
時間不長,平時與我經常在村里紅白喜事上走動的朋友們知道消息也趕過來了,而且有的人已經將我們村莊的先生也請來了,一時間一些經常在紅白喜事上當總管,禮房先生及其他有關的鄉親們也過來了。
鄉村普通老百姓的白事,雖然不需要什么治喪委員會,但普通老百姓的白事,也是一件大事情,輕視馬虎不得。白事上當天一般主家都要在自己院門的對面墻壁上,用白紙寫上“當大事”三個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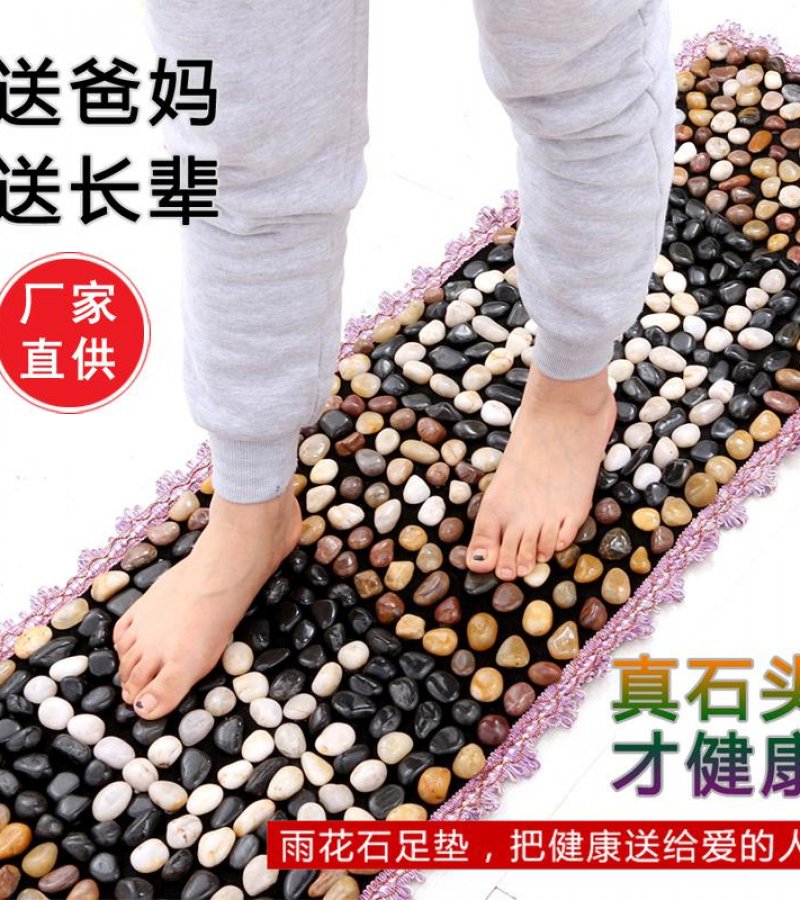
說明了人們對于白事的重視。
最主要的還要安排打穴,砍引干拴(墳墓上栽的柳樹),砍哭喪棒,安排人員送孝。送孝就是通知主家親戚朋友出殯的日子,根據男方,女方,親戚關系的不同,分別送不同尺寸的白布,而送孝最主要的是通知到逝者的人主,人主就是逝者娘家最直親的人,因為一般白事上主家最怕人主無端挑剔,所以白事上主家都將人主捧為上客。
還要 安排訂制紙扎紙花等,還有出殯的早一天晚上的燒“見紙”等,事無巨細,面面俱到,什么事情都要考慮到,安排到。
而出殯的日子,也是有講究,從亡故之日三天至七天不等,逝者年歲不到xx歲三天出殯,xx歲以上一般是五天頭上出殯,而一些高壽老人謝世則存放七天,而且還被稱為喜殤,請音樂響器,雇戲班子,當作喜喪來辦。
但也有一些例外,那就是季節氣候天氣的原因。

我們當地農村還都是土葬,逝者亡故以后大多是在自己家里停靈辦孝,一般季節不要緊,但如果趕的五黃xx月,大數伏天,氣候炎熱,加之那時候農村條件不好,時間稍長恐怕逝者的身體腐爛變質,所以采取三天出殯的辦法。
我父親逝世正趕上五黃xx月,那年夏至過后的第十天,正是氣候炎熱,容易腐爛變質的時候,于是,也是根據情況采取了三天以后出殯的辦法。
但我父親的安葬是合葬,與我的生母合葬。
原來我父親與我繼母再婚的時候就商定,我父親百年以后,與我生母合葬,而我繼母百年之后再回歸到孝義,與她的第一個丈夫那里合葬,孝義還有我繼母的一個親生女兒,侄兒甥女,最主要的還有原來繼母第一個丈夫的本家當戶,人丁興旺事業有成,也是我繼母百年之后回歸孝義的一個始作俑者。
這個也是我父親與繼母的生前約定,同時也是我們當地喪葬的一個風俗。

而父親要和我生母合葬,首先是要找到我生母的墳塋。
我生母是上世紀xx年去世的,距離我父親去世已經過去二十多年的時間了,中間經歷了高級社,公社,特別是那時候的農業學大寨運動,大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平田整地,平墳造地,將所有的墳墓都攤平(集體化到土地下戶的時候,我們村莊所有的墳墓基本上都攤平了),但雖然墳頭沒有了,年代也不少了,可具體地段,大置還是依稀記得。
于是,第二天上午我與五六個前來幫忙的鄉親們去到了我生母的墳地,按照大置尋找。
那片土地低洼下濕,屬于鹽堿地一類,很大一片土地沒有莊稼,只有一些雜草,這就給我尋找生母墳地創造了一些便利的條件。
于是,我按照原來依稀記得的位置,首先將帶來的供品擺上,點上蠟燭,燒上高香,表黃紙,敬美酒,祈求生母在天之靈保佑盡快找到墳塋,祈求過往神仙保佑事情通通順順。

然后,就開始尋找,五六個人有的人用鋼釬探,有的人用鐵鍬挖。記得那天晴空,艷陽高照,毒辣辣的太陽烤的人悶熱難當,時間過了近一個小時了,仍然是沒有一點影形,隨后又擴大了尋找的地方,仍然是一無所有,時間已經到了上午的11點多鐘了,當頭的太陽烤得人汗水淋漓,看看那幾十平方米的地方探測過的痕跡,我不免有一些灰心了。
是否年代久遠自己記憶的位置不確切?又是否農業學大寨時候平田整地將我生母的干骨已經拋撒了(記得我們當地當年農業學大寨大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平田整地挖渠修路的時候,往往有好些無主的墳塋被挖開,黑黑的未腐漚了棺材板,人的尸骨散落一地),不得而知。
眼看將近中午12點了,太陽當頭,空曠的野地里,沒有一絲遮陰的地方,加之兩個多小時的勞累,人們也有點筋疲力盡了,正當我無計可施,考慮是否放棄的時候,突然其中一個叫范春富的鄉親叫道;
“你們快看,這里是什么?
”

范春富是我們一個生產隊的,那時候,他正是年輕力壯,而且他父親是我們村里的一個紙匠,可能他也耳聞目睹對于一些喪葬方面的事情,有些傳承,加之他細心,做事情有覺眼(有覺眼當地土話指懂行有眼光)。
我們頓時眼前一亮,順著他手中的鐵鍬一看,只見到他鐵鍬翻出來的土中間,夾雜著一些黑黑的好似棺木腐爛了的木屑。
“找到了!
找到了!
”一個以前曾經幫助人們尋找過干骨的人,胸有成竹興奮地叫道;范春富也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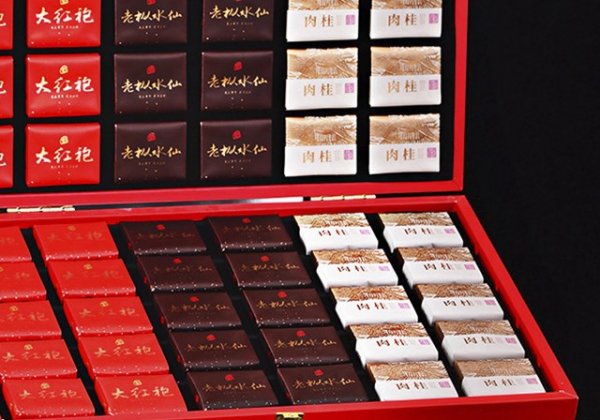
“可能是吧!
”于是,幾個人一同發力,三下五除二就將上面的一些土挖過,繼而,里面的磚瓦,和衣飯缽相繼漏了出來。
我們當地的風俗,磚瓦是記載逝者的生辰八字和卒時候的年月日,好像是帶點的意思。
而衣飯缽是一個大約高十幾到二十公分左右,粗大約十公分多一些的陶瓷小罐,在安葬起靈的時候,由逝者的直系親屬將靈前供獻亡者的祭席及貢品有選擇地填進去,然后再用金銀紙裝裱起來,下葬的時候放到棺材的上面。
當時,磚瓦沒有什么印象,倒是那個衣飯缽,雖然在地底下經歷了二十多年,我在生母去世時候,也僅僅xx歲,但是,我還依稀記得那就是我小時候,父母親他們用來罐肉(罐肉是我們當地舊時用來加工豬羊等肉制品的一種做法,就是將豬羊等動物肉,切成小塊,放上調料放到一個我們當地叫做罐肉罐罐的小陶瓷罐中,放到火上慢火煨熟,我們當地叫做罐罐肉)的一個小罐罐做的。

確認無疑,我非常欣慰,畢竟二十多年的時間過去了,能夠在那么長的時間,在墳頭全部攤平的情況下找到,這也是非常不錯的(那時候我們那里就有好些人家的墳塋找不到的,給后人留下了不少的遺憾)。
于是,大家小心翼翼地將上面的土鏟去,生母的干骨也即將露出天日,這時候,范春富是害開(害開當地土話指知道認識)之人,他趕緊叫另一個人將帶來的雨傘撐起來,擋住太陽光,以免我生母的干骨見到太陽。
這個也是我們當地的一個風俗講究吧!
意思可能是亡者已經到了陰曹地府,不能夠再見天日了。生母的干骨露出來之后,就由另外兩個人來揀拾,而揀拾干骨這個在我們當地也是有所講究,一般正常人是不做的,意思是怕有所防犯,對后輩兒孫不利,所以大多數由當地的一些孤老,或者沒有后輩的老人來揀拾。
兩個人仔細地將生母的干骨都揀拾的放到事前準備下的紙箱子里,然后將上面蓋一塊紅布(也是怕有所沖撞),兩個人抬到與我父親合葬的墳地里,釘一個木頭箱子重新入殮,等第二天與父親的墓穴合葬。
面對生母的干骨,我不免唏噓不斷,感慨萬千!
這些干巴巴的骨頭,就是生我,育我的母親嗎?這就是小時候經常聽人們說起親我,念我,疼我的母親嗎?
這就是小時候昏暗的煤油燈底下一針一線,千針萬線給我縫制百家衣的母親嗎?
事實真不可思議,但事實就是如此,人生百年誰無死,自有后人來傳承。這是人生的規律性,誰也不能幸免,死死生生,死死生生,一輩流傳頂一輩,自有后來人。